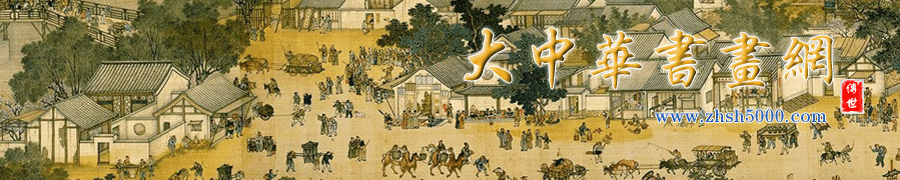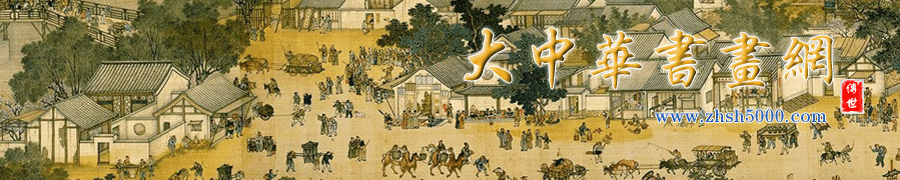五四以来,就有人认为汉字“确实到了山穷水尽,非变不可的地步”,后来也有人说,“认识了旧文字的根本缺点,我们就可以肯定改革的必然性。”他们共同的论据是:除了中国,全世界都采用拼音文字,可见其正确和进步性。
然而,汉字的历史至少五千年。汉字的成熟伴随着书法艺术,艺术的伟力塑造汉字品格。笔者认为,简化汉字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适用,为图眼下的小便利,置汉字理据于不顾,强使艺术就范实用,焚琴煮鹤,喻之不过也。比如,早有学者举例说“乾”字简化成“干”,那么“乾隆”就得写成“干隆”,后来的《简化字总表》把这一意见作为特例收入说明当中……
简化汉字中过于急促粗糙的原因何在?我以为,大众崇拜,西方崇拜,是20世纪中国人的亢奋源。在简化汉字工程中,两大崇拜的驱使力得以合流。
以汉字简化的目的,是为了大众、为了便捷为依据,而责难中国文字落后繁难,以为西化(拼音化)才是最终归宿的观点,似乎无懈可击,但笔者仍不得不发问:将便宜的工具交给大众,又如何使民众得到艺术、美感与诗?或者说,谁断定大众只需要工具,不需要诗、美感与艺术?
笔者以为,惟大众是从、惟庶民是尚的民粹主义,是20世纪意识形态的主调与基调。正如章太炎早年指出的:俄国本是拼音文字,文盲照样很多——民粹主义的后果是精英主义没落,百日戊戌维新,是精英主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天鹅之歌”。
而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对汉字命运的同情,似乎远比我们深厚,他说——
“有一些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坚持使用他们的文字系统。在形式上,汉字比字母更为有趣和优美;系统的内容也更为充实,比如一页《人民日报》所包含的信息要比一页《纽约时报》更为丰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人不愿将他们珍爱的文章付之于口语稍纵即逝的发音。
而这恰恰是欧洲人所做的。字母是表音符号,西方人在他们的文字中仅仅记录词语短暂的发音,而不是意义。因此,西方的文字不可分割地和所有音韵的变化与多样性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音韵的变化和多样性在任何语言中都在所难免。每当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发生变化,每当语法和词法出现新的发展的时候,文字便要跟着一起变化。每当一些说特别方言的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随之需要有配套的文字和文献。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当拉丁语不再是欧洲统一的语言的时候,便发展出五花八门的民族语言和文字。现在,倘若欧洲人要阅读五百公里以外或是五百年前的文字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汉字是表意符号,其所记录的是词语的意义而不是发音。因此,尽管也像所有的口头语言那样,音韵和其他的变化在中国亦屡屡发生,但汉字系统却无须被动地追随所有这些变化而变化。即以本章所举的少数例子也可证明,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能够阅读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和任何历史时期撰写的绝大多数文献,即便其完成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因此,文字在中国成为保持文化一体性和政治体制稳定的最有力的工具。
正因为发展出模件系统,使他们可以处理这个集合,所以这一切才能成为现实。只有靠模件系统才能够设计、使用并记忆数千个不同的字形。也只有靠模件系统,汉字才能够实现其真正的功能:确保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连续性。这种令人敬畏的统一性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汉字本身的字形演变,由篆而隶,而行草,而正楷,除于方便适用的因素之外,一直有一股巨大的动力,来自艺术创造的冲动,或者说,是全民族的形式感和审美追求造成了一部与汉字发展史相交融的书法艺术史。
如果说识字困难的话,习字更不易。但书法却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为普及的一门艺术了,从一般人的识文断字、记账尺牍,过年家家户户门上的春联,到文人墨客的诗文唱和,皇室宫廷秘不示人的书法真迹,价值连成的法帖碑拓,可高可低,可俗可雅,可大可小。
正是由于对名家真迹的爱好和临摹的需要,使中国人在公元8世纪前后就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后来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造纸和印刷技术出现后,人类的文明才有了今天看得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