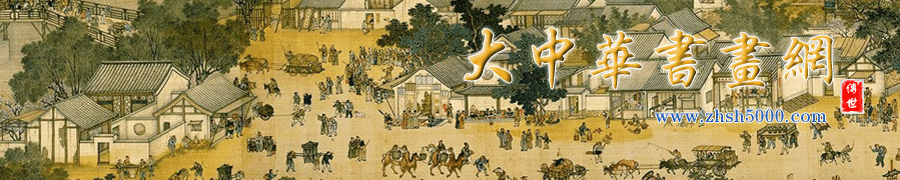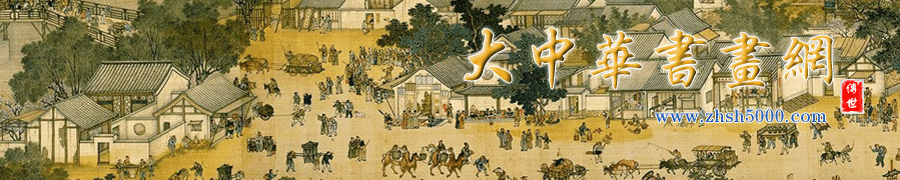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西陵峡》是傅抱石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山水作品之一
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那些日子里,一切都是新的。旧的东西也被人们期望赋予新的意味。这时候,无论是电影、戏剧还是音乐,都在用浓重的笔墨描绘着新生活。
1949年4月的《人民日报》出现了那场著名的“国画讨论”。4月22日,《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以“国画讨论”为题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25日,发表江丰的文章《国画改造第一步》,作为“国画讨论”之二;26日,发表王朝闻的文章《摆脱旧风格的束缚》,作为“国画讨论”之三。这些讨论提出:“深切地感受到国画有急需改革的必要,使国画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地适应于广大人民的要求,从而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此前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80余位画家参与的“新国画展览会”。
当时国画的处境是艰难的,如何顺应时代,成了中国画避免被时代淘汰的关键。
这时的傅抱石,和大多数中国画家一样,正陷入一种空前的苦恼中。当时的人们出于政治和教化的需要,要求美术要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和新时代的风貌,作为一个注重继承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家,如何用自己的画笔来表现这一切呢?
这是画家走出书斋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始,徐悲鸿在《漫谈山水画》中写道: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度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并也无其他积极作用。其中杰作,自然能供我们闲暇时欣赏,但我们现在,即使是娱乐品,顶好亦能含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现实主义,方在开始,我们倘集中力量,一下子可能成一岗峦。同样使用天才,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不更好过石豀、石涛的山水吗!
这是一个画家走出书斋的年代。
一股自觉将自己的画笔流放到大自然中去的巨大潮流,正冲刷过整个美术界。
山水画家们决定走出去,到大自然中寻找出路。用中国古人“外师造化”的方式,走出一条独特的路。
早在1954年,李可染和张仃、罗铭已经在江南开始了他们的写生旅行。3个月后的北京,在北海公园悦心殿,“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开幕。
沉寂的国画界热切地关注这次展览,人们从苦闷中又看到了希望。李可染们发现了中国山水画的新路。
写生,到大自然中去,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画如何“反映现实”的问题,一时间蔚然成风。除了李可染等人的江南写生,著名的还有黎雄才、关山月的武汉防汛写生,石鲁的陕北写生,傅抱石、关山月的东北写生,关良的访东德写生等。
而这一切,都为傅抱石率领江苏画家进行的“二万三千里写生”埋下了伏笔。
二万三千里写生
1960年初冬的一天,长江客轮“民众号”驶离了重庆朝天门码头,开始了它又一次三峡之行。
这是一次注定被载入美术史册的长征。
从1960年9月15日开始,身为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傅抱石,率领钱松岩、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一行13人,在3个月的时间里,途经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东,行程二万三千里,进行了史上路线最长的一次写生。这也是一次开宗立派的长征,从此,以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开始在美术界叫响。
这年11月13日深夜,江苏画院党委书记、画家亚明站在“民众号”客轮的顶层甲板上,望着西陵峡江面上闪烁的航标灯,一动不动地呆了很长时间。这是长江上新出现的事物,在50年前的江面上,它们显得那么新奇,那么引人注目。
这些江面的灯火,指引着船只在夜色中安全地航行。在亚明的眼中,这不仅是现代的科技,而且是长江航运史亘古未有的新一页。他决定画一张表现航标灯的画,他觉得这可能比画很多的三峡风景,更有现实意义。这是一个新奇而大胆的决定,因为国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表现过这样的光影景色。这幅名为《川江夜色》的画后来在《美术》1961年第3期发表,画家发自内心地讴歌着年轻的国家。航标灯闪烁着,启发了无数的美术青年:只要去创造探索,国画也可以表现火热的时代。
故地重游的傅抱石一直到长沙以后才开始动笔。和很多画家的写生习惯不同,傅抱石常常是只看不画,或者只是简略地画几根线条的速写以帮助记忆,他把饱览沃看的大好河山,全部印在自己的记忆中。
《西陵峡》是傅抱石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山水作品之一,也许是在“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创新思想的激发下,傅抱石借鉴历代山水皴法,结合对地质学的研究,创造并丰富了“抱石皴”技法。
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笔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成了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抱石皴”法在他所喜用的皮纸上将西陵峡表现得苍劲雄健、水墨淋漓、意境浩瀚。画面构图饱满,峰不见顶反而愈显其高耸挺拔、气势磅礴。冒着浓烟的轮船,这在传统的山水画里是罕见的,在这里不但没有破坏山水画特有的意境,反而调和了顶天立地的山峰带来的咄咄逼人,为这幅巨作增添了悠然的气度。
后来,老舍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傅抱石先生的画》的文章,里面写到:“我真爱傅先生的画!他的画硬得出奇……有人也许说:傅先生的画法是墨守成规,缺乏改造与创作。我觉得这里却有个不小的问题在。我喜欢一切艺术上的改造与创作,因为保守便是停滞,而停滞便引来疾病。可是在艺术上,似乎有一样永远不能改动的东西,那便是艺术的基本的力量。假若我们因为改造而失掉这永远不当弃舍的东西,我们的改造就只虚有其表,劳而无功。”
在艺术的坚持和创新的平衡上,老舍对傅抱石有着强烈的认同。
黄土高原的风光
当江苏写生团到达陕西的时候,傅抱石遇见另一位知己——大名鼎鼎的石鲁。
当时如日中天的石鲁,是来自延安的老革命,与大多数画家相比,他的级别更高:十一级干部,30岁就执掌陕西一省的美术。石鲁是中国画坛少见的天才画家,当时,他的《转战陕北》、《逆流过禹门》、《东方欲晓》等在美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以他和赵望云、何海霞为首的“长安画派”的大名,已经冉冉升起。他们描绘的黄土高原景色,突破了千年来山水画的表现程式,为当时的美术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
火车到达西安,石鲁来迎接。出站时,亚明悄悄地对傅抱石说:石鲁为您预备了二斤西凤酒,放在宾馆窗台上了。
令画家们一见如故的,不只是对美酒的共同爱好。黄土高原的壮观让江南的画家们激动不已。这是一片从未有人用国画表现过的领域,粗豪而又敏感的石鲁,将自己的天才画笔伸向了这里。
在石鲁热情地陪同下,傅抱石也将黄土高原的风光收入笔下,用他特有的“抱石皴”的笔法,绘出了《陕北风光》:高原上劳动的队伍、行驶的汽车和冒着烟的工厂,是当时要着力表现的内容,目的是为了体现欣欣向荣的建设场面。这是傅抱石的代表作之一,他用自己熟悉的笔墨手段,表现了全新的对象。
他们的下一站是华山。
待细把江山图画
明代著名的江南画家王履是古代画家中少见的以写生见长的画家。他的不朽名作《华山图》画集细致入微地描摹了这片神奇的山峰。几百年过去了,同样来自江南的画家们踏着前人的足迹来到这里,期望能见到自己心中的华山。
钱松岩是一位勤奋的老画家,每到一处就忙着打稿。亚明则随时随地发现华山的美,甚至上厕所也不错过,忘记了自己的原始“使命”。一路上,傅抱石多是打打速写小稿,或者到处走走,看其他画家认真地记录着。这位团长在写生团里显得非常悠闲。
傅抱石的悠闲和其他团员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年轻的画家黄名芊对此感到疑惑。回到成都,一路上只是画画写生稿的傅抱石终于开始有了激情。黄名芊的疑惑也随即揭开。
1960年11月1日,傅抱石回到成都宾馆,先是喝了一点四川白酒,这是抗战八年他在重庆就熟悉了的味道;待到微醺,又点燃香烟凝神静思;待思考成熟,抓起山马毛大笔,竖扫三两笔,画面主峰便呼之欲出。很多年后,黄名芊依旧记得这“当时下手风雨快”的情境。
华山素以“险”闻名于世,但傅抱石没有具体去描绘险绝处,而是以飞动泼辣的“抱石皴”作“大块文章”,气势雄阔、奔放。山腰间以留白形式表现缥缈不定的云彩,山脚则写平缓坡地,以衬托华山的“高耸云端、壁立千仞、奇峭无伦”的气概来。华山仿佛成了一个生灵,岿然不动,却焕发着新的风貌。
这幅名为《漫游太华》表现华山西峰的画,成为傅抱石画风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他将画面拓宽,题为《待细把江山图画》。
这幅横空出世的作品,被认为超过了明代画家王履的《华山图》。
2000年,傅抱石去世35年了。黄名芊决定将40年前傅抱石领导的江苏画家写生团的经历写成书。这一年,写生团的老画家们,大多已经去世了。健在的除了老领导亚明,就是几位当年年轻的学生。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文艺方针。画家们的努力,推动了新山水画在20世纪中期的发展,把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以写生带动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一个历史高潮。就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中国画完成了它的历史蜕变,又一代美术巨匠们用突围的方式登上了艺术的舞台。60年后的中国,中国画画家们接过先辈们手中的画笔,挥毫泼墨,图画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