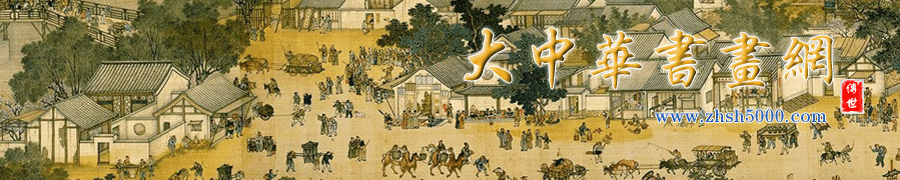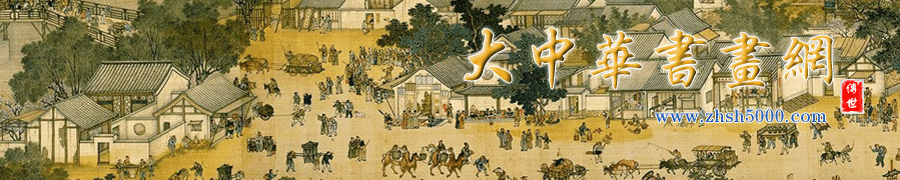吴冠中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让无数喜欢他的人难过不已。忽记起几年前参加他的一个画展,许多场景历历在目。那天几家博物馆在故宫联合为他召开了研讨会,一时间好评如潮。看着大家如此评价自己,他没有说话,半途就退场了,也许是不喜欢那样的热闹吧。这一幕,给我很深的印象。
“失恋”于文学,“移情”于美术
吴冠中的绘画成就,在美术史上自有定论,那是我们这些外行所不必置喙的。从我个人的兴趣来看,他在美术上的引人注意,大概和文学的梦想有关。身在画坛,又有文学写作的冲动,进入文学又不属于文学,得诗文的理趣,遂有妙意。连他自己也是承认的。在《沧桑入画》里,他说:“前几年曾和汪曾祺先生交谈,他说平生一大憾事是没有从事绘画,我说正相反,我遗憾没有从事文学,我们都老了,已无法互换。”在《双燕》一文里,他又说:“中学时代,我爱好文学,当代作家中尤其推崇鲁迅,我想从事文学,追踪他的人生道路。但不可能,因为文学家要饿饭,为了来日生计,我只能走‘正道’学工程。爱,有多大的魅力!她甚至操纵生死。爱文学而失恋,后来这恋情悄悄转入了美术。但文学,尤其是鲁迅的作品,影响我的终生。”
吴冠中赴法考试的试卷,是《试言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他的答卷文采飞扬,能够看出他良好的文字功底。他在法国读名家的画,自然也读文学。在画风里,也有诗文的美,彼此相得益彰。他很喜欢蔡元培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西方绘画近于建筑,东方绘画多似文学。那么在美术里有文学的影子,那是自然的了。
在《我负丹青!丹青负我!》一文中,他再次说:
我彷徨于文学与绘画两家的门前。
……
绘画之专长是赋予美感,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这是文学所达不到的。任何一个大作家,无法用文字写出梵高画面的感人之美,语言译不出形象美。而文学的、诗的意境也难于用绘画来转译,比如阿Q和孔乙己的形象,就不宜用造型来固定他……齐白石利用花鸟草虫创造了独特的美,是画家的荣幸,他提高了社会的审美功能,但这比之鲁迅的社会功能,其分量就有太大差异了。我晚年感到自己步了绘画大师们的后尘,有违年轻时想步鲁迅后尘的初衷,并感到艺术的能量不如文学。文学诞生于思维,美术耽误于技术。
这段话似乎注释了他晚年为何不断写随笔、散文的原因。他对文学的痴情,不亚于美术。而对一些文学观念和美术观念的注意,都丰富了他的创作。
许多作品离经叛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他还没有后来的名气,吴冠中曾到绍兴写生。留下的几幅作品都冷峻、清秀,好似染上鲁迅的底色。画面简洁多味,颇多传神之笔。许多意象透着无言的苦思,对命运与天人之际的面对,有神灵的飞动。民俗的与神异的猜想都有,似乎是东方哲思的闪烁,让人心动。他后来曾说,自己喜欢李清照、李煜、李商隐,一直想成为一名有力度的作家。虽无法抵达其路,而精神上要攀援的,恰是鲁迅那样的高峰。
鲁迅给他的不仅是人格的力量,还有诸多哲学与美学的启示。比如《野草》里的《过客》走向神秘的未知的意象,他深以为然。艺术的趣味就在于在没有路的地方走着,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探究。还有一个参照在于,不惜成为文坛的公敌,也要孤独地走下去。通过对古典艺术的借鉴和外来艺术的拿来,自成新体,也大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而且他赞佩鲁迅“横站”的气魄,认为自己后来能够自行其路,得益于鲁迅的“横站”。
我读吴冠中的画,觉得是远离八大、吴昌硕的路径,有了现代主义的东西。他不太使用旧文人的笔意,而是借用传统的技法,做现代式的表达。抽象与写实,神意与诗趣都在这里,绘画语言较之传统的文人是多了新意的。印象里他的绘画没有齐白石那么巧小、隽永,也缺乏张仃焦墨山水的大气,但他仿佛天外来客,是一种神奇的美。他赞美石涛、林风眠、潘天寿,却不袭其旧路,而自寻新途,许多作品都离经叛道。有一点旧山水画的笔意,又多见印象派的墨痕。在一些地方摄取了林风眠的想像力,一些地方又有明清文人的古意。最终一切都是自己的,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在一新一旧之间,走了别人难以重复的路。
“笔墨等于零”的言论
与鲁迅“汉语拉丁化”的思路接近
晚年的时候,他对美术的看法,常常出言不逊,争论多多。细想一下,在思路和意识深层,和先锋文学的精神是相同的,那些思路也与鲁迅思想叠印在一起。从五四以来,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文白之变,文言文式微以后,初期的白话文是多样化的,汉语表达的各种可能性都出现了。后来汉语的发展渐渐出现了问题,尤其是今天,白话文的魅力在丧失,而且它的多样可能性被各种各样的因素阻挡着。也缘于此,人们都在渴望着中国的白话文的内力喷发。文白之变之后,汉语是不是还能够具有深远的意象,又有现代性的因子,这其实是近二十年来文学史的研究者们不断考虑的问题。我觉得吴先生的探索和文学界的探索很像。其实美术界也在思考一种表达的维度,如何能够超越我们已有的模式,突破这个极限,使艺术的表达具有别样的气象。吴先生其实是用美术的实践回答了文学史家思考的问题。
吴冠中似乎是先锋派,但其实也有古中国读书人的脾气。他的表达方式很有意思,我认为关于“笔墨等于零”的爆炸性的言论,其实跟当年鲁迅批评汉字思路是非常接近的。鲁迅灵活地把握了古汉语之后,看到了走出古汉语的意义。他觉得要靠拉丁化,用拼音文字来解决语言表达问题。这是一个冒险,其中未必没有偏执的一面。他的穿越传统,进入新的精神维度的智慧,还是把汉语的空间拓展了。废除汉字不意味着不用中国话。吴先生虽然说笔墨等于零,他的线条表现的意象,其实容纳了古中国的许多精神,也有现代个性知识分子的东西。他的笔墨没有士大夫气,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民族很多画家笔墨里有酸腐味,这是难以摆脱的旧迹。鲁迅当年参观了几个画家的画展,却没有什么评价,我猜想就是觉得我们画家身上还保留中国传统文人的惰性,背着重重的包袱。如何能在现代表达方式、表达维度里具有个性又不失东方固有的优美,这是近一百年来许多人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和吴冠中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吴冠中给文学界另外一个启发是,他的经验的表达具有颠覆性,很少重复自己,不断探讨多元书写的路径,即智慧表达逻辑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他具有强烈的生活挫败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其画里看到轻灵冲淡和肃静之美,似乎没有受到黑暗痛苦的折磨,他把这些东西深深隐藏在画的背后。他的画面呈现的质感,超越了生活的苦难,把记忆升华成典雅的美,一种气韵生动的东西。不愿简单地还原生活,对人生有着梦一般的猜想,世俗的意象纷纷掉下,而升腾的是迷人的图景。或许他以为,创造别样的世界比摹写现实更为重要。只会一种思维,不能超越传统与现状的人是没有出息的。绘画与文学其实是人的心灵史的不同表达式。我在吴冠中先生的笔墨里倒是读出了文学史家们期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