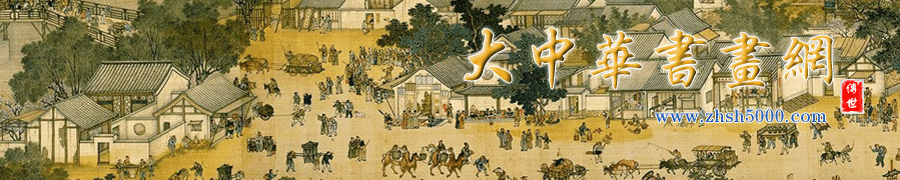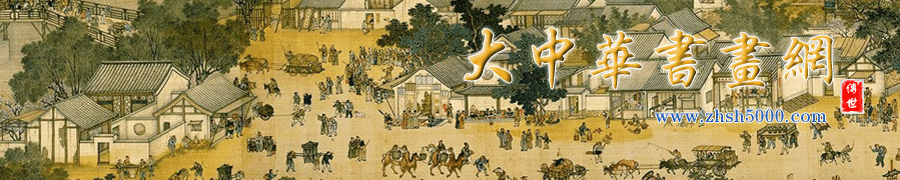张小平,林学明,一位是著名的跨界艺术家、广告人,一位是国内最大室内设计公司的总裁。20多年前,他们的身份是同一个:中央工艺美院七七级学生。他们最为敬重的老师是同一位:刚刚去世的吴冠中先生。
写生不是画“风景明信片”
张小平说,吴冠中先生当时是系里的普通老师、基础课教员。“‘文革’十年,吴先生没能站在讲台上,所以他对我们这些‘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与热情。” 林学明这样认为。“我们很有幸。在一年级和三年级时都上过先生的课。先是色彩课,后来是写生课。”
张小平回忆,吴老师带他们下去写生,自己也在创作。他的特点就是当“搬运工”———“从来不集中一地画‘风景明信片’式作品。他教我们要‘边采石头边炼矿’,就是看到哪里的山、水、树、房子合适就存入胸中,到创作时‘杂取种种’,用画笔‘搬’来你的作品里。他说,‘写生写生,关键在于‘生’,而不是‘写 ’。”
随吴冠中写生的那段日子,是林学明大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白天,老师带我们写生,晚上他就和同学们聊天。”赴居庸关写生,当时45岁的吴冠中和大家一样,两个馒头、一瓶水就是一天的干粮。他还随着一帮年轻人风风火火地“爬煤车”。“居庸关那边山坡坡度大,火车开得慢,人可以抓着车皮搭一阵便车,”林学明解释道,“老师还特别喜欢背北方农村拣牛粪、羊粪等的‘粪筐’。把画板、画笔统统放进去,背在身上,方便省力!”
张小平还有个很深印象,就是吴先生写生的时候不吃午饭,沉迷其中。后来他在北京机场画《北国风光》时,张小平陪他一天,也是看他从早到晚不吃饭、不喝水。“老师一工作的时候就什么都顶得住,身体好像都没有了饥渴的感觉。”
“他们不是来见我的家具的”
从外表上看,张小平觉得吴先生“完全就像一个生产队里的生产队长,而不是什么概念中的艺术家,跟普通阿伯一样,没有任何作派,没有形象设计”。
当年,吴先生家就住在北京后海的一个大杂院里,后来搬到方庄带电梯的公寓楼,也还是小小的三居室。房间里的陈设,“起码是像25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感觉。我们去,还看到墙上有溅到的颜料,老师也笑着不在乎。”张小平还回忆起听老师讲过的一件趣事,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法国有个代表团要去吴冠中家拜访,外交部负责接待的官员看吴家房子太差,决定把他的家具全部更换后再接待外宾。吴冠中死活不同意,说:“那个人是来见我的,不是来见我的家具的。”
艺术上要鼓励“培养叛徒”
“艺术上要‘培养叛徒’”,这是吴先生30年前对张小平说过的话。“他一直觉得,应该有独立思想、行为、作品风格的人才能成为被社会认可的艺术家。实际上,他一直是新中国主流美术的‘叛逆者’,一直是呐喊‘形式主义’的独行者。”张小平的理解是,我们国家曾经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提倡“内容先行 ”,吴冠中则觉得美术的核心是“美”,美就应该首先表现在形式上。
“吴先生总是说,每一个艺术家的成长,一定是在前一个艺术家倒下之后!这也正是我们做他学生的难处,要做吴冠中的叛徒谈何容易啊!”张小平感慨。
吴冠中的中国水墨创作一直面临毁誉参半的局面。张小平说,30年前吴先生就曾对他说:“中国画的门这么高,这么大,你不给我进,我就不进,我就在门口铺一张席子。”言下之意是说艺术的门是不由得权力来开关,对国画艺术的探索终会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吴先生的性格。生前,他从未平静地生活,总不安分守己,处在风口浪尖上备受争议,腹背受敌仍坚持己见。”
“中国的美盲比文盲多”
毕业二十年间,学生们跟老师时有书信来往,但见面不多。“原来我们同学都觉得,老师时间不够用,还是不要打扰他。但现在想来他也应该很寂寞,有次去拜见他,因为路上车子出了问题迟到了,看到老师一直在窗前张望,而泡来等我们的茶都凉了。” 张小平说。
张小平与吴先生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今年的二、三月份。“老师来电,说他收到了我寄的东西,就是在广州地铁一号线,我利用一些没有灯箱广告的位置做了一个吴冠中作品展。老师常说,为什么艺术品一定要在美术馆里呢?我们的社会,扫文盲更要‘扫美盲’。”当时张小平觉得老师精神不错,也没有听到他患病的消息。
“老师直到4月16日住院前,才放下了画笔。”林学明缓缓说道。上个月,林学明到香港观看吴冠中“独立风骨”的展览,在展品中惊讶地发现了恩师写有“故土”二字的画毯。“那是先生使用多年的画毯。我隐约有感,他是要离开了吗?……”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刘玮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