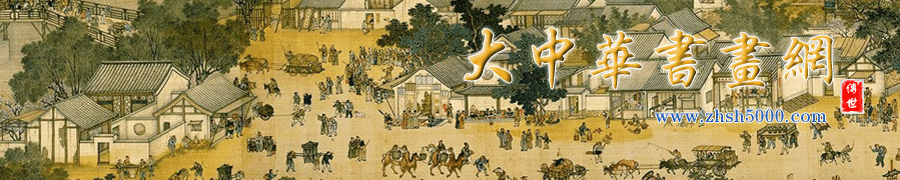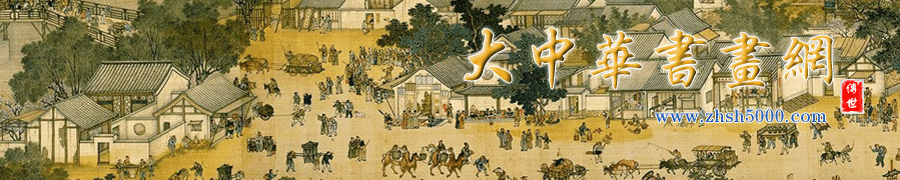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由文字演变而成的艺术。这种转变并不是在文字之外另起炉灶,而是汉字本身原始的内在品质的自然升华,是由汉字的特质决定的。
汉字的创制是先民对他们生存的自然界的认识和对自身生命感悟的记录,他们将所认识的概念概括成一个个独立的图文,使早期汉字一定程度上有着与物象之间的对应性,具备了“象征”特征。虽然这种对应性不是完全绝对的,但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察而可识,识而见义。而象形只是文字的表象,表义才是其终极目的。当然,除了以形表义外,汉字也有以音表义的特性,所以汉字的特质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就文字的“义”而言,必须通过“形”来表达,而文字的“形”,只是通过书写一途才能表现,因而,书写与文字的关系是直接而密切的。进一步讲,书写即是体现汉字“形”的手段。通过对“形”的书写,实现表“义”的目的。
汉字的“形”是为表义目的服务的,由于汉字的象形特征,使它的“形”本身就是千姿百态,风情万种。这与生俱来的生动性,使汉字的“形”虽无色彩而具图画之美,反映这种图画之美的手段是书写,当书写的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汉字的“形”便被赋予了某种精神意义,一直隐藏在实用性之下的汉字的艺术品质便得到了发掘和培养,所以汉字的艺术性是包孕在“形”要素之中的固有品质,当书写者自觉地利用书写来表现某种寄托时,汉字就完成了“形”的升华,具备了它作为书法艺术的独立性。
汉字书法的艺术性在汉代就被明显意识到了。随着人们对毛笔性能的掌握和运用能力的加强,对文字构形理解程度的提高,体会到书写的过程可以带动情绪,尤其是奋笔挥洒之时,更能使人体会到一种心手相应的快感,人们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追求这种享受。那可敛可散的笔锋,可轻可重的笔触,可疾可徐的速度,竟能带来千变万化的线条情绪,吸引人们不顾一切地投身于此,感受着不同的线条情绪所带来的不同节奏、韵律的趣味,快意十足,直至废寝忘食。一时间书写的风潮靡漫整个社会。东汉赵壹《非草书》对人们书写的狂热性和痴迷程度作了描述:“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汉代草书《殄灭简》中那自在飞扬的笔势,连属圆转的用笔,《甲渠简》的用笔爽利,迅捷剔挑,让我们禁不住会想见其挥运之时,随着它们的用笔节奏一起呼吸。而汉代张芝《冠军》《终年》帖的云龙雾豹,出没隐现,变化无方,用笔练达精熟,潜气中行,古质俊雅,更是书法所达到的时代高度的杰作,很显然,书法给人们提供了寄托情怀的天地。魏晋时期,这种书写表现能力已然成为士人竞相追逐的技艺,并以此扬名立身,赢得尊重和自信,书法艺术充当了士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王献之“每作好书”寄与谢安,谢安或“题后答之”或“裂为校纸”,王献之因谢安将自己的信札作答后送回而未作保留,视为对自己书法的不认可而颇感懊丧。王羲之则自信自己的书法跟汉代名家钟繇张芝比或可抗衡,他为卖扇老妪所书扇面题字,交代但言出自王羲之手笔,可得一百钱,足见他的书法已为人宝爱。这一时期,书写的艺术品质越来越完善成熟,书法成为一个自觉的艺术活动,书写作为艺术的独立性终于得到确立。尽管人们早已被书法艺术感染得如痴如醉,为更深刻地感悟书法艺术对心灵魔幻般的召唤,不惜卧划被、墨池水,但以书名世者一直没有专称,直到唐代怀素在《自叙》中评价颜真卿书法时说“颜刑部,书家者流”,才首次使用了“书家”概念。怀素自己虽幼而事佛,但并不以坐斋诵经为能,而是凭所怀书法绝技,奔走于豪门权贵,他在人前作书,往往借酒助兴,顷刻间写满粉笔长廊数十间,他的草书线条变化奇无定则,不主故常,时而似暴风骤雨,时而似轻烟古松,时而似山开万仞,时而似走虬奔蛇,观者无不为之倾迷。怀素将书法艺术由士人内在修养的功能推向了表演性,不仅自身感受了书写过程中的亢奋,也从人们的赞扬声中获得心理的满足。李白专为他作《草书歌行》以称颂。在书法的艺术性逐渐确立的同时,书法的社会功利性也相伴而生。唐代取仕制度明确规定“身、言、书、判”四大原则,书法直达干禄之途,成为士人必需的荣身之阶,至此,它的艺术性和功利性高度统一。唐代因善书而博得朝廷格外垂青者诸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自有与当朝皇帝多一重精神交流的渠道,唐太宗追捧大王,王羲之书法便成为衡量得失的唯一标准,以投上之所好;宋代大兴趋时贵书,以交结仕宦,书法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明代沈度以其平整朗秀的书风而得明成祖喜爱,赞其为“我朝王羲之”,他的字被定为朝廷御文诏诰的专门用字,一手妙笔带来的荣耀是任何东西无可替代的。至于清代科举中的状元,更是大多写得一手精妙的颜体字。
艺术的本质在于对精神有所诉求。书法艺术正是通过用笔的方圆转折、速度的疾徐、墨色的浓淡枯润等来表现线条韵致,通过字结构对空间分割的均衡欹侧、朝倚向背体现构型的性格,通过章法的整饬错落、疏朗茂密来表达相应情调。当文字的书写以通过种种手段达到某种倾诉与寄托为目的时,它就脱离了实用的母体,染上了艺术的斑斓色彩,它的识读价值在保留文字表面意义的同时,又深入扩展到抒情的层面,唤起了人们心中或明快或凝重、或磅礴或空灵的审美感受。所谓“晋书如仙,唐书如圣,宋书如豪杰”,就是对不同时期书法艺术的时代总风格的总结。在汉字的“形”作为对实用的“义”起说明作用时,书法是从属于文字的;当“形”的书写目的完全从实用“义”的母体剥离掉时,文字与书法之间的原始主从关系得到彻底颠覆,这时的文字只是书法借来挥洒尽兴的躯壳,至于文字是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表现得怎么样以及如何表现。晋书虽仙,但仍不失常态,右军所言“放浪形骸”,实为逸气所存,唐书言圣,多指真书,而怀素草书则彻底摆脱了文字实用的羁绊,狂气冲天,他的《自序帖》秉承汉代张芝唐代张旭之遗风,将艺术的纯粹性发挥到极致,观者目之所及,会下意识地被那行云流水般的线条牵引视线,而忽略字义的识读,最终会陶醉在他满纸的浪漫与流美之中。至此,书法从实用中脱胎换骨,在达成它向艺术品质转换的终极意义上缔造了胜古绝今的又一高度。
汉字的线条构造和象形特征使得它具有先天的审美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上古文字时会产生审美愉悦的根源所在,也是汉字在“形”的要素发展过程中,能够最终脱离实用性,成为独立存在的书法艺术的根本原因。汉字的母体中包孕着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尽管它的艺术性获得了独立,也只是从这一母体中分离出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以书法艺术无论如何发展,汉字都是它赖以存在的永恒载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是艺术的通则。中国书法是符合这一通则的,它的实用性服务于生活,它的艺术性则满足了人们形而上的精神需求。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展现形式,它所发挥的作用在每一方面都具有人类文明所需要的含义。